
【学术档案】
胡焕庸(1901—1998)地理学家、中国人口地理学奠基人。江苏宜兴人。1923年国立东南大学毕业。192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1928年起历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教授。1950年后历任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人口研究所所长等职。193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人口地理学,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等值线人口密度图。著述甚丰,遍及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领域。主要有《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世界气候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等。
人们知道胡焕庸,大多是因为“胡焕庸线”——1935年,34岁的青年科学家胡焕庸亲手将代表全国4亿多人口的浩若繁星的点子落实在当年的中国地图上,疏密之中一条暗含着中国人口分布规律的线呼之欲出。这条线建构了中国人文地理学自己的话语体系,也是认识中国人文地理结构的重要工具,今天已作为中国最醒目的人文地理标志被写进了中学和大学的地理教科书。
“胡焕庸线”,是胡焕庸近70年研究生涯的惊鸿一瞥,也是他早年便达到的成就,而他留下的学术财富,远不止这一条线——从这条线开端,他开创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科。中国地理学会甚至认为胡焕庸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人口地理学,他带动了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为了追赶时间,80多岁的他依然站在学术前沿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曾这样描述科学家的使命:拨开迷雾,认识世界,最终在纷繁复杂中把规律性的、稳定性的东西找出来。而胡焕庸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
上世纪80年代,丁金宏成为胡焕庸的博士生,那时胡焕庸已经80多岁,这样的年纪还在高校工作,放在今天也不多见。“胡老先生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的名誉所长,但这个所长绝不是单挂个名字,他就没离开过研究前沿”,丁金宏说,在他们来华师大的前几年,胡老先生还与助手一起写了几个大部头,包括《中国人口地理》《世界人口地理》——这两部著作可谓是国内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他们去了之后,胡焕庸先生每年还会有文章发表,比如《中国人口区划》,老先生觉得这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因此还出了英文版。“到了这个年纪,他还一直在思考问题,只要在家里就不停地想、不停地写。他这么高年龄又不图什么。”丁金宏记得,晚年胡焕庸先生还带着华师大人口所每年出版《人口研究论文集》,“每期的头几篇几乎都是他做的”。1990年,89岁的胡焕庸正式搁笔,同年出版的《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选编了他有代表性的29篇著作,书中附有1924年到1990年的几乎全部著述目录,其中完成于搁笔前十余年间的著述有90余种,占总种数的一半以上。尤其是1985年到1990年间,胡焕庸平均每年发表成果10.4种,用学生吴传钧的话说“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竟然出现了他一生中最高产的奇迹”。以至于有人致信给胡焕庸,问他是不是原来的那个“胡焕庸”:“感觉时间已经很长了,怎么媒体还在介绍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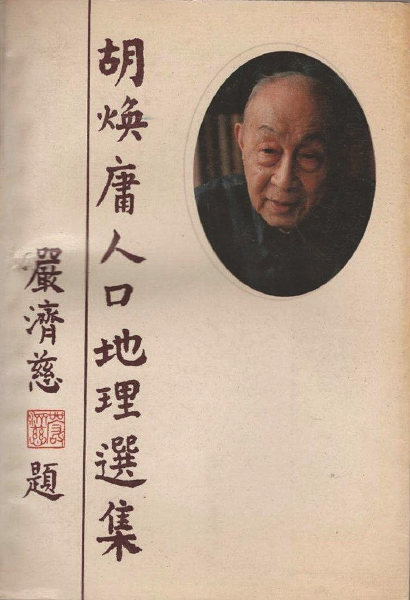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1984年胡焕庸开始招收博士,第一届只招了一人,中间停了一届后,1986年重新开始招收,名额一下子提到三个,丁金宏就是三人之一。投报胡焕庸门下的细节,丁金宏还记得很清楚,那年,准备继续攻读地理学博士的他决定“认祖归宗”,便从南京致信在华师大任教的胡老先生表达了意愿。几天后,老先生给他回了信,这封信让丁金宏很是好奇:信纸上的字迹抖得厉害。到了上海才知道,当时85岁的胡焕庸右手已经抖得不能写字,为了对抗这种不便,老先生开始学习用左手书写。而从胡焕庸的文章里可以了解,那时衰老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读书都需要借用高倍放大镜才能进行下去。而即便如此,他也想尽办法把学术研究进行下去——他口述,请人代为记录,晚年的科研成果多数以这种方式呈现于学界眼前。
“他很急,急着要在地理学领域再多做点学问”,这是第一次正面接触老师后,丁金宏的感觉。“我们到华师大考博士生,考到最后一门课时监考老师说,胡老先生很想先见见你们”,丁金宏当时觉得很意外:还在考试,导师就要求见面,放在今天是不可想的。“见面后,他很恳切,说只要我们考试过了就可以去他那里,我能感觉到他那种需要有人跟着他把人口地理学研究推进下去的迫切心情。”后来,随着关系的亲近,丁金宏愈加感受到老先生对做学问的那份急切。当时胡焕庸就住在华师大一村,附近因为造楼常常哐哐响个不停,并不是个做研究的好环境,但他还是保持着每天清晨起来看材料、写东西的习惯,8点半到9点还会走出家门到办公室看看大家的工作情况。对于这种急切,丁金宏曾从胡焕庸先生处得到一个解释——“年纪大了”:“他说,你们年轻人时间是按年算的,而我是按天算的。”但丁金宏觉得这只是原因之一:“据我所知,他青年时代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后来他在‘文革’中浪费了十多年,所以更加珍惜时间。1978年他重归学界,一句怨言也没,第一时间就重提了被中断的人口所的事情。”那也是胡焕庸第三次开始人口地理学的研究。与学术研究分别多年,国际上相关科学研究的发展突飞猛进,而胡焕庸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几十年收集的图书资料也荡然无存了——他决心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呼吸一日不停,工作一日不止,努力争取夺回我在十年动乱中白白浪费掉的宝贵光阴,为祖国的人口地理学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余热”,这是80多岁的胡焕庸在《我和人口地理学》中留下的字句。事实也是如此——“写了6本书,约100万字”,这是1982年胡焕庸对自己三年工作的一点总结。胡焕庸的小儿子胡企中谈及父亲时也说,他的晚年生活十分“单调”,惟有看书写东西,社交活动很少。
或许在老先生的眼中,什么都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障碍,除了时间。他也一直试图把这一心得作为治学经验传于学生。照顾到老先生年纪大了,丁金宏等几个年轻学生没事的时候都尽量少去打搅,但是胡焕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叫他们过去,一方面听听汇报,一方面给他们讲最近的时鲜事。“他总是先问你最近有什么想法、做了什么,如果没达到他的预想,他就会让我们关注什么领域,经常说出一个东西来,我们都很惊讶,有一些我们年轻人都闻所未闻。这个时候,他就会叮嘱我们要抓紧时间。” 胡焕庸1993年为庆祝《地理学报》创刊60周年写的文章已经在关注城市化的空间过程、城市居民的空间行为,那时就提出大城市里出现的民工潮问题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加强,认为保障人口、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将成为21世纪多科学研究的主题之一。90多岁的老先生在文中,一再提到“新方法”“新技术”“科学交叉共研”,眼界之新令人赞叹。丁金宏等几位学生对老师追赶知识的速度也曾纳闷过,直到去图书馆、资料室借书才揭晓了谜底:“图书馆里的书尤其是外文文献,很多都用铅笔做了标记,我们当时就很奇怪。后来知道地理系要进的外文书都是胡老先生亲自去订的,他特别重视外国的研究信息。”胡企中深知父亲研读学术原文的习惯:“他说,你要在学科前沿的话,就要把原著看到。他50岁学俄文,马上就可以用俄文作为工具来了解当时苏联的有关信息,并用于他的著述之中。”有书为证,1956年,胡焕庸出版著作《苏联自然地理概论》,全书用俄文资料写成。除了英语、俄语,胡焕庸还通晓法语、德语,日文也是很早就学会了,一个亲戚告诉胡企中,他和胡焕庸十几岁时同时开始学习日文,一人买了一本日文书,“他说,待下次碰见我父亲,我父亲已经在用日文看材料了,他还在背字母。我父亲这个人,抓住了就会钻下去。”所以,不难理解“文革”后恢复工作,胡焕庸就先关注到了上世纪70年代整个地学界盛行的洋底扩张与板块构造学说,还在学习这一全新理论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世界海陆演化》一书。“他说过地理学界的人应该跟上地学革命的步伐”,胡企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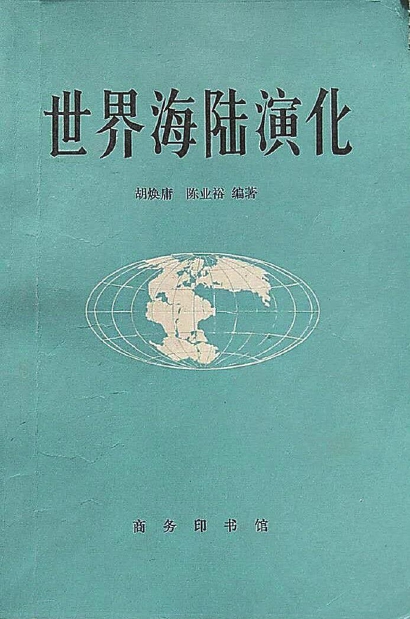
《世界海陆演化》 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是地理教育家,是地学专家,还是治淮的“智库”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书林》杂志多次向胡焕庸约稿,期望了解他“年过八旬、眼花手抖,还要一股劲儿研究人口地理”的原因,胡焕庸在文中的回答表露了初衷:上小学、初中时,史地教师经常讲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如何入侵,人民生活如何贫困等等,潜移默化之中,胡焕庸“深深爱上了地理这门学科”;后来上大学,师从竺可桢,“悄悄懂得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内容和作用”,就此把它定为终生钻研的目标。
因为“胡焕庸线”的学术影响力太大,胡焕庸被定位为人口地理学者。但在很多熟悉胡焕庸的人眼里,他是个通才,“是地理教育家,也是地学专家,人口地理只是他个人学术活动中的一小块领域”,胡企中谈及父亲时这样说。翻看集其一生学术成果的《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仅是目录就能窥见这位老学者涉猎范围之广:“黄河流域之气候”“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世界经济地理”……单是区域地理书籍就著了十余种,对苏美英法德日等国家和中国的许多省市都有专书论述;所著的《中国之农业区域》更是我国研究农业地理与农业区划的开山之作。胡焕庸深受法国学派影响,强调人地关系论,他从不把人口或其他的地理要素孤立起来研究,在他眼中,地球是一个整体,关注人地关系的地理学就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统一的学科。因此,他能够在各领域间转换自如。
“胡老先生如果被逼到某个领域,就会在某个领域特别钻。但最感兴趣还是人口,一旦有机会还是会回到人口地理。”丁金宏介绍,胡焕庸先生1953年回归学校,还是很想做人口研究,后来于1957年成立了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其间胡焕庸还前往南通等地进行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的调查,时间虽短已经有成果出来;后来人口研究成为禁区,他又转向自然地理,做气象气候,曾出过《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永远有新的研究题目”,胡焕庸的子女对此也深有体会,1960年前后,再次与人口地理暂别的胡焕庸转而从英法德俄大量文献中搜集资料,开了一门新课“古地理学”,讲授地球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各时代的气候演变和生物演变,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热爱地理学、热爱理论思考,但他从不做脱离实证的虚妄的‘理论’研究,他的‘理’都来自‘地’,来自实践”,《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地学卷)提到胡焕庸时,这样评价。胡焕庸强调地理学的实用性,也因此重视农业地理和水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淮河发生过两次大灾,灾后,胡焕庸曾带着几个学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走遍了苏北大部分地区,写成考察报告《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然而这本书的一些措辞触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神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1950年淮河水患又发,中央领导和水利部专家看到了胡焕庸关于两淮水利的书,便邀请他到治淮委员会工作,胡焕庸的名字又一次与淮河联系在了一起。治理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胡焕庸去了以后与工程部技术人员从皖北到苏北实地考察,提出了在苏北新开一套灌溉总渠,分引一部分淮水直流入海,并疏通中下游水道、在上游多建山区水库的建议,后为水利部和治淮委员会采纳。期间,兼任治淮委员会资料室主任的胡焕庸搜集了不少淮河流域的县志以及淮河水灾的资料,流域地势高下和河流历史变迁,在胡焕庸心中自有一本账,“遇到淮河方面的问题。哪个地方怎样,他们都问我,我马上回答出来”,胡焕庸成了水利部和治淮委员会的“大数据库”。借助这些资料,治淮三年,胡焕庸写了《淮河》《淮河的改造》《淮河志初稿》等书,为淮河的科学治理提供了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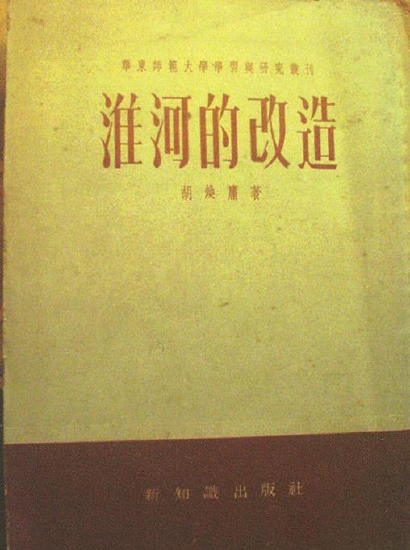
《淮河的改造》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重数据、地图,重创新思维,他传承的是学术、更是学风
学生朱宝树曾问胡焕庸,喜欢被称呼胡先生还是胡老师,“他说喜欢后者,因为先生谁都可以用,而老师能表明自己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个人”。成为教师的念头来自于胡焕庸幼时。胡焕庸的父亲是私塾先生,在他很小的时候积劳成疾早逝,母亲常常勉励他继承父业,当一个教师。高中毕业后,家境寒苦的胡焕庸适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免费招生,在10誜1的录取率里,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位,之后跟着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竺可桢专研地理和气候,后来也成为竺可桢最喜爱的两个学生之一。胡企中从亲戚口中得知父亲极为重师道:“竺可桢先生过南京,我父亲把他接到家中,老师坐着,他站着、两手垂着,毕恭毕敬。”
尊师重道,受业传承。胡焕庸非常看重地理学人才的培养,给学生上课,讲知识,也讲治学道理,“他常讲,治学要不断地做文章。地理学尤其要注意数据,没有数据就不是科学,没有地图就不成地理”,研究生时期胡老先生的叮嘱,朱宝树一直记得。这些叮嘱都来自于胡焕庸的治学经验——他发表的论文常常附录大量的数据,配以充足的地图,坚持让事实说话,让数据说话。
时间再往前一点,上世纪60年代,朱宝树是华师大地理系的大学生,那会儿胡焕庸给大学生们上课是这个样子的:“他上课时肩上扛一根指图棒,大地图一挂,就海阔天空地开讲,完全没有讲稿。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抓不住头绪,但是逐渐能体会出那里面有他的思想。他说治学就像瞎子摸象,越摸越像,这也是他治学的过程。”十几年后,朱宝树攻读硕士,又拜到了胡焕庸的门下,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胡焕庸定的。1980年前后阿尔巴尼亚赠予我国一万株油橄榄,胡焕庸注意到这些生长在地中海气候中的植物在同纬度东岸、水热条件组合相反的地方竟然生长良好,于是给了朱宝树一个研究题目——《地中海气候代表性植物油橄榄在我国引种的地理分析》。“胡老先生对新鲜事物很有感觉,有意无意地培养我们的逆向思维。我当时还不理解,但后来在我的研究生涯中,这种‘油橄榄思维’一直跟随着我,我也传给了我的学生。”而对于丁金宏的学生来说,胡焕庸1935年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是入门必须要看的几块内容之一。
胡焕庸桃李众多,朱宝树、丁金宏都曾任或正在担任华师大人口所所长,关注并推动着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发展。胡企中也曾很有底气地说:“解放后的地理学界骨干,基本上都是我父亲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时间到胡焕庸90寿庆的那一年,“没有大鱼大肉,仅是清茶水果,却是国内外学者群贤毕至,五代门生热烈祝词”,那是一场洋溢着浓厚学术气氛的寿诞会。
作者: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责任编辑:杨逸淇、刘力源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