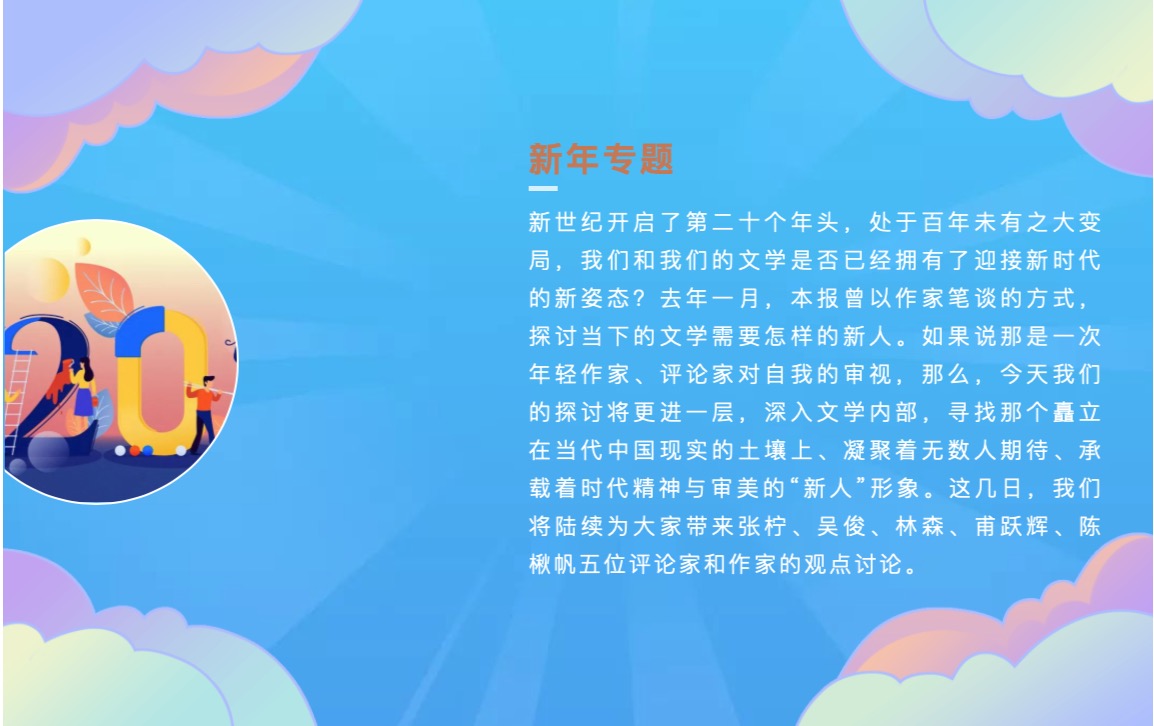

当下中国社会正进行着剧烈的变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如果经常看新闻,会发现,舆论相对更关注城市,尤其关注大城市里外来的年轻人。当然,也有很多舆论是关注乡村的,但无论关注的广度还是讨论的深度,似乎都“浅尝辄止”。而且,据我观察,新闻舆论里描述的乡村状况,是非常单一的。
2018年3月17日,新经济观察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访谈,《陈锡文:中国农村还有五亿七千万人,判断乡村情况要靠科学统计而不是返乡故事!》。访谈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这几年舆论场里很热闹的“返乡观察”。“和农业打了近五十年交道的陈锡文”说,那些回乡记录他大多都看过,“但那就是一个个‘故事’,故事具有特殊性,不一定有普遍性。”又说,“我们有三万多个乡镇,60万个村民委员会、317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状况怎样?作者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村、一个地方,整个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不可能靠讲故事完整地反映出来。破败的、黑恶势力横行的农村,肯定有,但漂亮的、发展好的农村也有……现在一提到农村,就说‘空心化’‘老龄化’。我就在想:那年年粮食增长,这粮食是谁打的?农民收入年年增长,又是怎么回事?”
陈先生这篇访谈在网上很容易搜到,在此不多引用。我很认同陈先生对乡村的看法。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对乡村的叙述,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空心化”“老龄化”等等。前阵子在成都,听徐晨亮兄谈论当下农村题材的小说,说关键词仍然是“村长寡妇大黄狗”。中国那么多乡村,为什么呈现在文学作品里会如此高度雷同?我想,不是因为中国的乡村雷同,而是写作者的思维实在太过雷同。

我们书写乡村,究竟有多少是来自自身当下真实的乡村经验或调查?有多少是来自对过去的怀念?
更有甚至,有多少是来自新闻报道或道听途说?我不是要否认乡村的“空心化”“老龄化”以及乡村凋敝、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这些现象,而是想说,还有别的模样的乡村么?至少,在我的个人经验里,乡村不完全是这样子的。
我在很多个场合,也在不少短文里谈论过我的老家。比如前阵子发表在《文学报》上的短文《村中岁月新》,写简阳荷桥村,牵出我老家的一些情况。但那篇短文,毕竟主要是写荷桥,在此想更具体地说一说我老家。
我老家在云南施甸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汉村。汉村可不像很多小说或新闻报道里说的那样破败凋敝,很多人家盖了或正在盖二层或三层的小楼,我家的是七八年前盖的,三楼顶上摆了很多大缸,种了火龙果、柠檬等;二层楼顶有个底部镂空的亭子,亭子四周和底下储满水,水里养着鱼。我回家趟在床上,夜深人静时候,能听到鱼在屋顶哗啦哗啦游动。汉村当然也有很多人外出打工,但留在城市的至今没听说过,打工只是权宜之计,赚了钱终究是要回来的,回来做什么呢?盖房子啊,汉村才是他们的家。相邻的几个村子,莫不如此。站在家里三楼楼顶望出去,到处是白色小楼,村落之间都是水泥路,村外田畴整饬,四季轮替,种了水稻、油菜、荷花或者小麦,有的不再种粮食,而是集中起来种葡萄、西瓜、梨等等经济作物。
这些是我老家乡村的外观,再说说老家的年轻人。村里年轻人是少了,但也有一些。打牌喝酒赌博的当然有,但也有一些在认真做事,从各个层面改变着乡村。
比如一个朋友承包了大片土地,做了一家农庄,种植洋芋等农作物,还种植大片桑树和草莓,让人去采摘。我也去过几次,吃到了很好的桑葚和草莓。这或许还不够特别,不够成为乡村的“新人”形象。那以下几位,或许足以称为乡村“新人”吧?
施甸银川村有个“壹坤窑”。“窑主”庆坤到外面学习烧制陶瓷的技艺后,回到村里开设了壹坤窑,自己做自己烧自己卖。上次我回老家,在庆坤家布置得鸟语花香的小院,亲自体验了一把做陶的过程——当然,我做出来的肯定是歪瓜裂枣。过了几天,开窑了,我们又去,发现还有几个人是从隔壁县来的,他们很快挑选了一批买走。那天,庆坤家恰好有水稻要收割,都在讨论收割机怎么进到田里。那可不是一亩两亩水稻,而是二十多亩。庆坤和相距不远的永华、永平兄弟一起租的稻田,说是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自己种了自己吃。庆坤的母亲和我们同桌吃饭,有点儿鄙夷地说,怕是五百斤一亩都收不起。
再说永华、永平兄弟。两兄弟一起合力盖新房,房子一共四层,面向院子的那面墙,整个一面落地玻璃。我头一次去,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样的房子出现在村里,和很多人对乡村的想象是严重不符的,甚至可以说,简直冒犯了那些觉得乡村衰败的人。永平原本在昆明电视台有工作,前几年选择回到村里来。永平说,他们盖这房子,还是和父母妥协后的结果。我想,如果不妥协,盖出来的房子会是怎样?
永华、永平兄弟还有更大的“野心”,他们和另外两位朋友,学斌、雪娇夫妇一起在深山里做了一处类似农家乐,但已远远超越农家乐的生活空间,叫做“东篱风雨”。这是升级了的乡村景观,田园、房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俨然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说起学斌,他虽然居住在县城,但来自农村。对施甸这样的边疆小县来说,县城和乡村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去年吧,学斌组织了很多同辈人,每到周末便到县城三馆广场边弹吉他唱歌,渐渐聚拢起不少人气,现在是挪到某地产老板提供的专门空间去了。到学斌家闲坐,和他父母聊天,他父母言语间,对他们夫妻做的这些事也颇不能理解。
讲这几位朋友的事情,我都说到了一点,就是他们和父母的“矛盾”。之所以有矛盾,不是因为利益冲突,而是因为观念相左。他们已经全然不是父母那样把自己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了。他们从旧有的乡村传统里走出来,成了全新的乡村年轻人。这篇短文的题目叫做“乡村里来了个年轻人”,自然是来自王蒙先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这“年轻人”怎么来的?不是像知青下乡那样,从城市里来,而是从乡村自身来的。
乡村自有其新陈代谢的一套运作规则,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看清甚至预知乡村的变化。
经常看到有些人感慨,乡村消亡了。真是笑话,我们当下活着的所有人消亡了,乡村都不会消亡。当然,也有人会说,感慨的是“传统乡村”消亡了。但我们感慨过“传统城市”消亡了吗?部分“传统乡村”已经在保护,这是另一个话题。我想说的是,我们允许城市不断更新,是否也该允许乡村不断更新呢?拿我身处的上海来说,现在的上海人有几个愿意生活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老上海?人类乡村几千上万年的历史,不是说没了就没了的,乡村自有其新陈代谢的一套运作规则,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看清甚至预知乡村的变化。

这阵子,展现乡村生活的网红李子柒引发了很多讨论。在博鳌论坛上,也有好几位同仁说到她,有的说她传播了中国文化,也有的说她美化了乡村生活。就在我老家,也有一位类似的美食网红,网名叫做“滇西小哥”,在网上也有几百万粉丝。她展现的乡村生活,没有李子柒展现的那样诗意,更接近本真,也更让我感觉亲切。但她展现出来的乡村,估计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大大美化了的。
这种觉得漂亮的乡村都是被美化了的认知,不是先入之见是什么呢?
李敬泽先生在博鳌论坛上作大会发言时说:“街上走着一个个农民,我们看得清他吗?还是我们带着一堆先入之见去写他?”比如前面说到的这几位乡村新“农民”,我们确定看得清他们吗?
面对剧烈变化的当下,我们且不要忙着做判断,且多看一看,多想一想吧。
当然,仅仅从个人经验不足以判断社会的发展。除了像陈锡文先生那样,有一个大的视野,还得有一颗冷静公允的心。博鳌论坛上,有一位前辈发言,说他回村看到有人在打麻将,那人站起来和他打招呼,想说“回来了?”却说成,“和了?”为此他说,乡村已经没有了灵魂(大概意思)。前辈是我很尊敬的前辈,但这粗暴的判断实在是我不敢苟同的。仅仅打个麻将,仅仅说错一句话,乡村就没灵魂了?乡村的灵魂也太脆弱了吧。那城市呢?城市人打不打麻将?城市有没有灵魂?
当下的舆论似乎有一种焦虑,普遍认为乡村的人就想着往城市走,小城市的人就想着往大城市走。看到过好几个类似的帖子,讲漂在大城市的人回到自己生长的小县城或乡村后,连个歌剧院都找不到了,没法“安放灵魂”了,找不到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了。但现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说真的,我虽然长期待在上海,但每次回到老家施甸,从未有过没法“安放灵魂”的感觉,也从来没有找不到一个人对话的感觉。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没有哪一种生活是“终极”的值得追求的生活。到了小城市得去大城市,到了大城市得到北上广,到了北上广得去巴黎纽约,那到了巴黎纽约还要不要去月球?大城市生活有大城市生活的美好,乡村生活也自有乡村生活的美好。歌剧院是很狭小的,歌剧院外还有大自然和整个宇宙。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资格去俯视生活在乡村的人。我们可能自认为没法和他们“对话”,可他们就稀罕和我们“对话”么?
进入城市,也要了解乡村;贴近时代,才能理解中国。希望有一天,我能写出不一样的当下乡村中国。
作者:甫跃辉
编辑:张滢莹
责任编辑:李凌俊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