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的突破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从内部突破传统框架的动力,因此呈现循环往复的特点,只有在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传统框架才得以打破,并迈向近代社会。这就是学术界熟知的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一种近代社会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局的风起云涌以及欧美内部的矛盾重重,一种新的史观开始出现,这就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即在中国发现历史,该史观强调中国近代发展在于其内部的力量,而非西方的外力。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强调西方前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并不具有优势,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即英国本土煤炭的利用和新大陆市场的开拓,是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启动的根源。虽然彭慕兰的观点有待于商榷,但这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是西方国家海外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标志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使每个后起民族肯定本民族在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从而明确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是作为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这一历史浪潮中。
** 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
该书集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为一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填补空白的著作。
首先,该书妥善处理宏观与微观叙事之间的关系。在六七十万字的篇幅中,作者纵览400年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以宏观的视角叙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作者又能够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立论中心,进行许多精细的描述,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入的剖析解读。因此,宏观叙述和微观分析通过作者之手,在《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一书中完美地呈现出来。作者以四个世纪作为一个考察单位,却没有落入那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窠臼,而是宏观和微观同时兼顾,既见森林也见树木,宏大叙事的架构下,包含对单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细致入微的描述。
该书的第二特点是有力驳斥了“西方中心论”。作者认为,中西思想的传播不是单向,而是双向:“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唯有读到介绍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西文译著,才算是真正的互动和交流,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他们最大的贡献就在这里——他们通过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在西方人的眼前展示了灿烂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图景,从此,孔子的大名远播西欧,中国成为启蒙时代欧洲思想家向往的文明的样板。”从这个角度看,作者认为,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吸纳并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那么马克思主义无疑含有中国思想文化的元素。
该书第三特点是研究资料丰富,文献多样化。首先,文中既有中文资料,也有外文资料,既有自家之言,也有他家之话,这对一本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来说,无疑增添本身的可信度。例如,该书提到《剑桥17世纪哲学史》肯定中国哲学在促进欧洲近代哲学产生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用来支撑作者认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结论。其次,在叙述近代以来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作者采用的多是原始文献,例如《民报》《万国公报》《新民丛报》等具有影响力的报刊资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最后,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并重。我们既能读到每个时代的原始文献,也能看到当今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西马”互动完成大转型
自从明末利玛窦携西学从南方进入中国以来,期间经历清朝自1723年禁教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将近120年西学处于被禁止传播的历史,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西方侵略者的大炮轰开,西学又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尤其到了19世纪末,中国真正迎来了一个西学全面东渐的时代,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从东、北方系统地传入中国。在接近400年的历史中,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中国思想文化也传到西方,推动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最终以先进西方哲学的最新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传到中国,这场哲学革命洋溢着一种批判精神,其成果必然是“中西马”三派在冲撞式的互动中达到新主流的形成。“中西马”三学的互动完成了二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正如书中所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时,它就能化成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继而转化为强大无比的物质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具体实践和中西思想交往的必然结局,是400年来“中西马”互动和融通的最高理论形态和最新思想成果——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思想主线,也是作者的创新理论和写作宗旨。
《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是一部优秀的理论著作,也是一部展现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的佳作。但是,瑕不掩瑜,指出书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是有必要的。第一,虽然作者兼顾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平衡,但限于篇幅,注定作者只能选取一些重要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片段,而遗落一些次要但也不是不重要的部分,例如一些不是那么有名但也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第二,书中突出知识分子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却很少关注底层人群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的身影。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从内部突破传统框架的动力,因此呈现循环往复的特点,只有在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传统框架才得以打破,并迈向近代社会。这就是学术界熟知的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一种近代社会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局的风起云涌以及欧美内部的矛盾重重,一种新的史观开始出现,这就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即在中国发现历史,该史观强调中国近代发展在于其内部的力量,而非西方的外力。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强调西方前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并不具有优势,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即英国本土煤炭的利用和新大陆市场的开拓,是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启动的根源。虽然彭慕兰的观点有待于商榷,但这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是西方国家海外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标志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使每个后起民族肯定本民族在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从而明确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是作为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这一历史浪潮中。
在众多肯定本民族参与世界近代化进程的著作中,张允熠教授的《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商务印书馆2021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作)是其中一本,也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在600多页的篇幅中,作者以高度凝练的手法把四个世纪中西思想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浓缩在其中。从明末利玛窦携西学进入中国开始,然后历经曲折的清朝中期,最后随着晚清以来西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思想、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终于汇成一股思想潮流,从而改变了中国的整个思想界,完成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旷古空前的主流文化大转型。“中西马”三派的互动是作者对推进中国四百年来思想文化大变局中的概述,从中西哲学的相识相遇来看,利玛窦携西学进入中国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源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史前史”,而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被接受是四百年中西思想文化长期碰撞与交流的结果,是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必然,中国思想界遂完成了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中西马”的合流。这一思想进程的逻辑,在《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一书中展现得十分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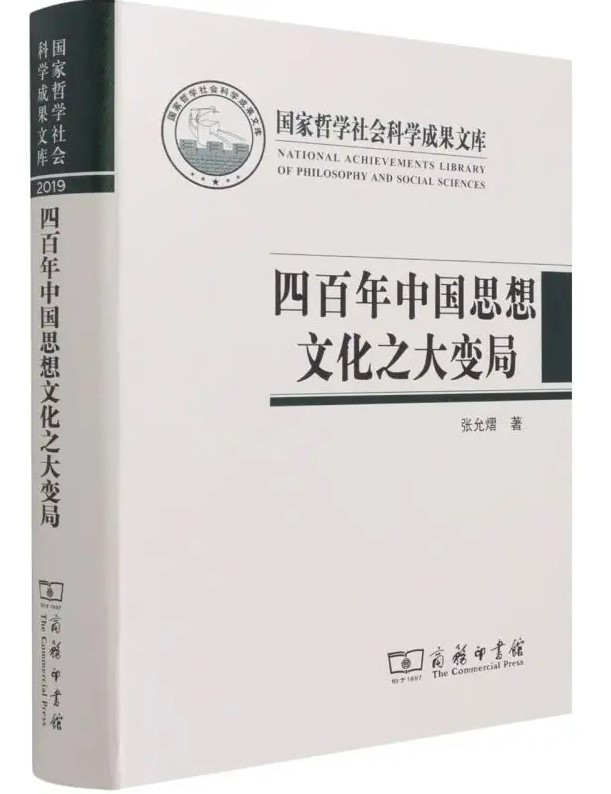
** 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
该书集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为一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填补空白的著作。
首先,该书妥善处理宏观与微观叙事之间的关系。在六七十万字的篇幅中,作者纵览400年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以宏观的视角叙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作者又能够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立论中心,进行许多精细的描述,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入的剖析解读。因此,宏观叙述和微观分析通过作者之手,在《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一书中完美地呈现出来。作者以四个世纪作为一个考察单位,却没有落入那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窠臼,而是宏观和微观同时兼顾,既见森林也见树木,宏大叙事的架构下,包含对单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细致入微的描述。
该书的第二特点是有力驳斥了“西方中心论”。作者认为,中西思想的传播不是单向,而是双向:“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唯有读到介绍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西文译著,才算是真正的互动和交流,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他们最大的贡献就在这里——他们通过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在西方人的眼前展示了灿烂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图景,从此,孔子的大名远播西欧,中国成为启蒙时代欧洲思想家向往的文明的样板。”从这个角度看,作者认为,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吸纳并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那么马克思主义无疑含有中国思想文化的元素。
该书第三特点是研究资料丰富,文献多样化。首先,文中既有中文资料,也有外文资料,既有自家之言,也有他家之话,这对一本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来说,无疑增添本身的可信度。例如,该书提到《剑桥17世纪哲学史》肯定中国哲学在促进欧洲近代哲学产生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用来支撑作者认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结论。其次,在叙述近代以来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作者采用的多是原始文献,例如《民报》《万国公报》《新民丛报》等具有影响力的报刊资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最后,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并重。我们既能读到每个时代的原始文献,也能看到当今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西马”互动完成大转型
自从明末利玛窦携西学从南方进入中国以来,期间经历清朝自1723年禁教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将近120年西学处于被禁止传播的历史,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西方侵略者的大炮轰开,西学又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尤其到了19世纪末,中国真正迎来了一个西学全面东渐的时代,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从东、北方系统地传入中国。在接近400年的历史中,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中国思想文化也传到西方,推动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最终以先进西方哲学的最新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传到中国,这场哲学革命洋溢着一种批判精神,其成果必然是“中西马”三派在冲撞式的互动中达到新主流的形成。“中西马”三学的互动完成了二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正如书中所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时,它就能化成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继而转化为强大无比的物质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具体实践和中西思想交往的必然结局,是400年来“中西马”互动和融通的最高理论形态和最新思想成果——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思想主线,也是作者的创新理论和写作宗旨。
《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是一部优秀的理论著作,也是一部展现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的佳作。但是,瑕不掩瑜,指出书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是有必要的。第一,虽然作者兼顾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平衡,但限于篇幅,注定作者只能选取一些重要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片段,而遗落一些次要但也不是不重要的部分,例如一些不是那么有名但也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第二,书中突出知识分子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却很少关注底层人群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的身影。
作者:陈恒(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系教授)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