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漱渝 |从罗素谈轿夫说起 | |
| 2019-12-12 13:48:07 作者:陈漱渝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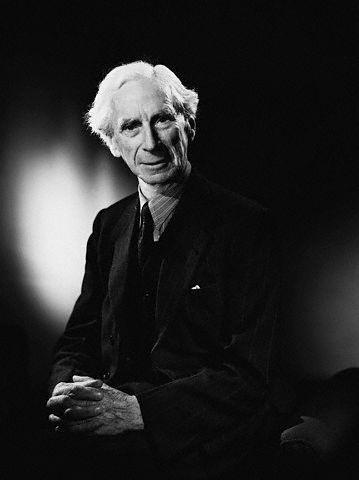
▲罗 素
我不懂哲学,没有研究过中外哲学史;对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最初印象完全来自鲁迅杂文。这种印象归纳起来有两点:一,他赞美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未必正确;二,他赞美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未必出自真心。
罗素1920年曾经访华,在杭州游西湖时遇到一群轿夫。归国后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我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坐轿子翻山。山势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让轿夫歇息十分钟。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作为一位外国友好人士,罗素说这番话完全出于善意。他认为中国人能够从辛劳中找出欢乐,在谈笑间化解纷争,而不是斤斤计较,时时抱怨。
然而中国文豪鲁迅却有另一番见解。他认为,赞扬中国固有文明的外国人,有的是不了解中国的实情,有的是希望中国人抱残守缺。有的则是完全出于猎奇心理,比如爱看中国的辫子、日本的木屐、朝鲜的斗笠……1925年4月,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写道:“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就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在鲁迅眼中,抬轿人跟乘轿者的关系不是一般服务人员跟顾客之间的关系,而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国的下层民众能掀翻这种人吃人的“人肉筵宴”,中国则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之林,“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鲁迅希望外国友好人士多疾首慼额地指摘中国的缺点,他会诚心诚意地捧献他的感谢。因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

▲鲁迅
1933年9月,鲁迅又在《准风月谈·打听印象》中提到罗素,写的是:“五四运动之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罗素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鲁迅的这番议论,是因英国作家萧伯纳1933年访华引发的。鲁迅的意思是,中国的现状,生长在中国的同胞自己应该心里最清楚,完全没有必要向外国人打听,只不过“小百姓”说话无人尊重罢了。鲁迅文中所说的急进青年是指当年新潮社的傅斯年和罗家伦。他们后来一个个进入了权力中心,却变得一声不响了。
对于同一社会现象,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审视,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作为一个外国游客,罗素赞扬中国轿夫的乐观友善,这不能说有什么错,至少跟那些充满种族歧视、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的“洋大人”有着本质区别。但习惯于进行逆向思维、致力于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鲁迅又有他过人的敏锐,超人一等的见解也使我十分佩服。最近,我认真读了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觉得确如美国哲学家杜威评论的那样,是“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罗素是在研读了大量文献资料,又对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才发表他的看法,并不是因为受到欢迎之后碍于情面才说一番捧场的话。
实际上,鲁迅跟罗素虽然看问题有时侧重面不同,但在中西文化观方面却有很多契合点。鲁迅提倡“拿来主义”,既主张保存“中国向来的魂灵”,又主张“采用外国的良规”。总之,鲁迅希望中国人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罗素也主张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和溶合,比如希腊师从埃及,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学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拜阿拉伯人为师……罗素肯定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智慧的做法,但同时指出不能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照单全收”。他希望中国人既保存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方法,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异的新文明,而不是“摧毁本土文化,代之以美国文化”。
罗素1920年的中国之行不仅在鲁迅作品中留下了历史记录,而且在毛泽东早年的革命史上也留下了历史记录。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署名“杨端六讲,毛泽东记”。
杨端六,原籍苏州,后迁居长沙,因为1885年端午节后一天出生,家人故戏称他为“端六”,是一位曾经留学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学家。他夫人袁昌英,曾跟苏雪林、凌叔华同在武汉大学任教,并称为“珞珈山三女杰”。1920年,刚从英国留学归国的杨端六代表中国公学、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上海、南京、长沙等地巡回演讲,自己也发表相关讲演。27岁的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被长沙《大公报》主编龙兼公聘为该报“馆外撰述员”,故担任了杨端六讲演的记录人。
根据毛泽东的这份记录稿,杨端六认为,罗素其人治学讲究实用,为人崇尚自由,在社会改造上主张调和。这三点也是英国人的共性。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罗素认为无非是发展实业和改良政治;而要达到以上这两个目的,一定要“用中国的药治中国的病”。在介绍杨端六讲演的同时,毛泽东还在他创办的文化书社出售了罗素的著作《政治理想》。
谈到政治思想,罗素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他对当时俄国革命也有所批评。今天看来,这些批评并不是全无道理。罗素晚年反对超级大国进行核武器竞赛,谴责美国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这些表现都十分难能可贵。罗素在数学和逻辑领域的学术成就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他跨学科的成就,1950年罗素还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最令我感动的是罗素对中国前景的展望。在中国四分五裂且被列强环伺的北洋政府时期,罗素就预言中国必将渐渐崛起成为远东无可争议的第一强国,并且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为此,中国必须自力更生,救亡图存,不能单纯依靠外援。他认为中国人很有必要培养爱国精神,但这种精神仅应用作防御,不应诉诸侵略;既不能让别人主宰,又愿意学其他国家的长处。他期待中国真正成为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能把吞食中国主权的外国强邦扫地出门,又留住中华民族持有的“温文尔雅,恭敬有礼之风,率真平和之气”。今天我们重读罗素1921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依然能感受到友谊的温暖和鼓舞的力量。
作者:陈漱渝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徐坚忠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