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众议: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82年获诺奖前“难产记”|了解125期嘉宾② | |
| 2018-10-02 11:31:35 作者:陈众议 | |

编者按:昨天(10月1日)开始,2018年度的诺奖获得者开始一一揭晓,今天的奖项缺少了“文学奖”,2019年将同时颁布两位获奖者。10月7日下午2点至5点,第125期文汇讲堂《让世界认识贾平凹》各界大牛云集。昨天我们已经感受了汉学家顾彬作为诗人的才情和睿智。今天的第二位是陈众议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是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专家。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刊发众议撰写、2011年再版著作《加西亚·马尔克斯传》的一节,描述马尔克斯获奖前后;以及陈众议的再版序,该序概述了拉美文学及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百年孤独》:憋了十几年,第一次书稿漏寄了一半
一九六五年十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的青睐终于真正地降临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头上。是晴日,他和妻子梅塞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度周末。行至半途,加西亚·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多年以后,奥雷良诺上校面对行刑队,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像一道闪电在他的脑际里赫然亮起。这就是憋了十几年的《百年孤独》的开头,这就是外祖母惯用的叙事方式。

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孕育十八个月的《百年孤独》(1967年第一版)
“我的小说着床了”,十八个月后难产出炉
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塞德斯说:“请给我十个月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墨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
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可以付印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八个月。
稿子是用复印纸打印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都交给了梅塞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孙。
梅塞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
除此而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庆贺呢还是应该哭泣。其时,梅塞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所有东西,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末了东赊西借,咬牙坚持了漫长的十八个月。
从《大屋》到《百年孤独》,整整耗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十八年时间。《百年孤独》脱稿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像往常一样,总想首先把稿子交给最要好的朋友阅览。他之所以这样做,一半是因为他多少还有一点胆怯的谦逊;一半是因为他对出版商们心有余悸,希望朋友从中斡旋。“出版商总是让我发憷,”加西亚·马尔克斯常怎么说。
稿子由梅塞德斯寄给远在巴黎的富恩特斯,邮资还是妻子拿仅存的首饰支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此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朋友的音信。
推荐者:这是“拉丁美洲的《圣经》”,出版社却拒绝
富恩特斯第一次听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五十年代末,当时姆蒂斯刚刚离开哥伦比亚到墨西哥定居。一天,姆蒂斯拿着一册《枯枝败叶》去拜访富恩特斯并对后者说,那是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所能见到的最好的作品。富恩特斯对姆蒂斯的话当然是将信将疑。是年他正在和埃马努埃尔·卡尔巴略主持《墨西哥文学杂志》,而且涉猎甚广,自以为不会有“大鱼”漏网。后来,他被墨西哥外交部派往欧洲供职,当他回来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墨城安顿下来。很快,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但是年轻一岁的富恩特斯一直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当作一个需要帮助、提携的年轻作家。
当富恩特斯收到《百年孤独》的时候,着实大吃了一惊。他一口气读完小说。他不禁喜出望外。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部足以与西班牙文坛的“圣经”《堂吉诃德》相提并论的惊世之作。第二天,他就把这部稿子寄给了一家西班牙出版社并给主编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称《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的《圣经》”。但是,稿子被西班牙无情地退了回来。于是,富恩特斯只好将其中一部分发回墨西哥并在朋友的杂志《永久》上率先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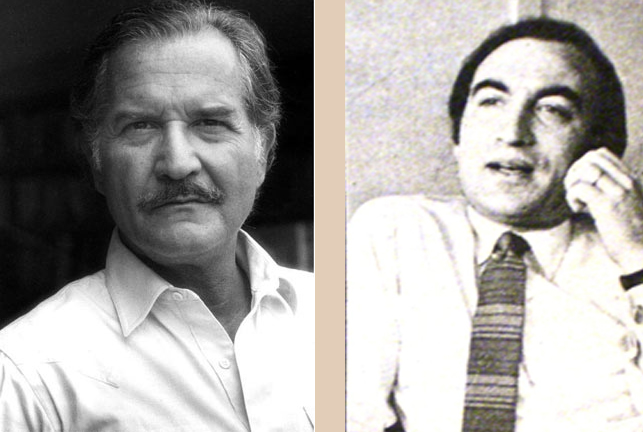
卡洛斯·富恩特斯(左)与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
对于这一段历史,没有任何人比《百年孤独》的“接生员”之一——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更加清楚了。其时,他正在南美出版社的《第一版》周刊任主编。他是这么回忆的:
事情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是1967年的秋末。几个月前,南美出版社的那个神秘、狡黠的文学部主任弗朗西斯科·波鲁阿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刚刚收到一部稿子,而且是从墨西哥寄来的。稿子不分章节,只有一些明显的空白。且不说纸张和邮包是何等的简陋,关键在于作者的头上高悬着两个沉重的判决:其一是SEIX BARRAL 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没有市场;其二是大作家吉列尔莫·德·托雷的批评,他用委婉的语气告戒作者,‘必须删除毫无价值的诗趣’。现在,我可以斗胆告诉精明的读者,那部书稿正是您所钟爱的《百年孤独》。
波鲁阿和我决定邀请它的作者参加我们主办的一次小说奖的评奖活动,并请他当评委,目的只是为了认识他。活动是由南美出版社文学部和我领导的《第一版》周刊举办的。为了欢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到来,我找来他的一幅照片做那期周刊的封面。我们很少有人听说过他,更没有人见到过他。所能找到的有关材料也只有路易斯·哈斯的《我们的作家》。哈斯是这么描绘他的:“敦实,留着惊人的小胡子,菜花鼻和满嘴的假牙……”那不是个地道的吉卜赛人了吗?波鲁阿和我就是带着这种印象到埃塞伊萨机场去迎接他的。是秋月的某个周末的凌晨三点。我们惊异地发现,无论是哈斯还是他的那些照片都没能展示他的真正特质:
他像风,不受梦幻和灾难的侵袭。他比吉卜赛人更加吉卜赛人,他是高康大转世。
然而,他和梅塞德斯度过了最最不公的三天: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然而,不知是最后的成功抚平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的坎坷,还是人们有意的忘却使事情变得合情合理、温馨可人了许多:人们只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像嫁闺女似的把书稿交给了梅塞德斯;梅塞德斯在对它进行了一番“梳妆打扮”之后,木讷地把它送上了前往阿根廷的旅途,而且因为邮资不足,第一次只误寄了后半部分。
一夜之间,西班牙语世界几乎所有人都在说《百年孤独》
一九六七年五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手拉手地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当他们行至某个博尔赫斯热衷并反复吟颂的街角,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地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那天,《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先睹为快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读者居然认出了它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他的心情比激动更加激动,他停顿了一下,像是犹豫,又像是震惊。最终,他学着海明威的样子,朝那人挥挥手说:“再见,我的朋友!”
第二天清晨,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在饭店旁边的一家咖啡馆用早餐。咖啡馆门庭若市。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一个临界的位置上,他不经意地朝人群张望,突然,他看到一位从早市上回来的家庭妇女的菜篮里居然明晃晃地摆着一本《百年孤独》。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指着那人的篮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梅塞德斯顺着他的手指,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百年孤独》。顿时,夫妻俩热泪盈眶。他们明白,《百年孤独》不再是一本单纯的文学作品,它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始为生命。
仿佛是要证实他们的成功,几天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参加了电台举办的一个读书沙龙。嘉宾主持罗多尔福·沃什是著名侦探小说家,在阿根廷拥有广泛的读者。然而,令可怜的沃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几乎是不请自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竟会喧宾夺主,吸引了当晚的几乎所有读者。人们像欢迎教皇似地欢迎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的说乌苏拉和他们的祖母一模一样,有的则断言阿马兰塔简直就是他们姨妈或者姑姑。
此后,《百年孤独》以每周一版的惊人速度从南美出版社的印刷厂产生并行销到整个西班牙语世界。
在一九六七年余下的日子里,在以后的许多年间,《百年孤独》成了创作界、出版界和读书界的共同话题。精神富有的人们,可能说不清哥伦比亚的准确位置,却不可能不知道《百年孤独》是谁的作品。
西班牙语世界震惊了。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百年孤独》,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书店都说此书已经告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端的是千金争舍,“洛阳纸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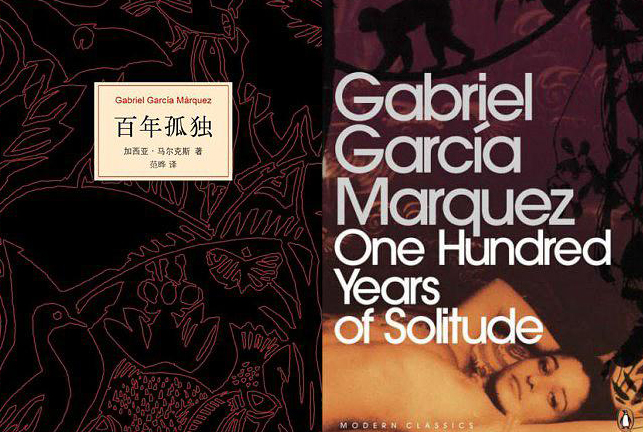
《百年孤独》的中文版(左)与英文版
马尔克斯成了世界上最不孤独和最孤独的人
世界震惊了。当年就有两家欧洲出版社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纪人卡门·巴尔塞尔签订了《百年孤独》的出版合同。不久,《百年孤独》的法文版和意大利文版出版发行,并在法国和意大利引起轰动。几个月后,卡门女士手中的翻译合同猛增到了二十多个,其中有德文版、英文版、葡文版、俄文版和丹麦、芬兰、瑞典、挪威、荷兰、波兰、日本、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包括克罗地亚语和斯拉夫语)、罗马尼亚等国的译本。卡门女士从中大赚了一笔,并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大赚下去,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给她的授权期限是一百五十年、利益分成为百分之十。这个合约是在一九六七年《百年孤独》出版前夕签订的,也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慧眼独具的卡门女士及其丈夫、墨西哥作家路易斯·帕尔马莱斯的一种回报。此后,卡门成了许多拉美和西班牙作家的代理人,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她乃是“拉丁美洲作家的格兰德大妈”。
由于《百年孤独》的巨大成功(它成了一家真正的无烟工厂,每天都在创造巨大的利润和崭新的纪录),加西亚·马尔克斯必须亲临巴塞罗那,和卡门一起去“数钞票”。
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最不孤独的人之一,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出版机构竞相邀请未恐后。
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最孤独的人之一,盖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
他出名了。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
序: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
终于有人以百万(而且是美元)的高价购买《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权了!
我对此早有耳闻,并听说卡门老太太(马尔克斯的出版代理人)的爱将小歌一直在忙活这件事。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它多少可以消除马尔克斯的一些偏见,比如他曾公开指责中国和他的祖国哥伦比亚“海盗猖獗”。同时,这也说明我们的一些民营出版机构确实已经发展壮大到了可以一掷千金却心不惊肉不跳的地步。至于是否重译、由谁担纲,我倒不怎么关心。随着出版业的放开、改制,名著重译早已蔚然成风。这一现象其实也早已无关乎译文质量。况且《百年孤独》原文并不复杂,更不是什么诘屈聱牙的东西。过去的译本如云南人民社、浙江文艺社的都相当不错。北京十月的译本最早,但忌讳处略有删节,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当然,翻译毕竟不是复制,其近真余地几近无限。我只希望新译本至少大体上不要逊色于以往几种。这一点,版权购买者应该比谁都在意。
受马尔克斯影响的一代中国作家

莫言等深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大陆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啻莫言或阿来、陈忠实?!我们这一代,甚至更老一点的和更年轻一点的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他的影响,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谓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并且发现了一两只“马脚”;但“当初却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就具体影响而言,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恰恰就是他那独特的叙事方式,他从第一句“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面对行刑队,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开始,行云流水般地发散开去。那是一种集神话叙述(集体叙事或集体无意识)与个性化叙述于一体的马尔克斯方式。其次是他的成功为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树立了信心。虽然他及他们那一拨拉美作家大获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冷战是个不可小觑的客观因素,但他们处理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创新、民族性与世界性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的方法无疑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中国作家大都看到了这一点。
魔幻现实主义是美洲的“第三河岸”
当然,魔幻现实主义不尽是《百年孤独》,它含括了一大批优秀小说。除却《百年孤独》,至少还有《彼得罗·巴拉莫》、《玉米人》《消逝的足迹》《深沉的河流》等等。它们的最大魅力无疑是重新发现并美妙地表现了美洲的混血文化。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集体无意识则是所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核心内容。传统使然,信仰使然,这些内容为美洲或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披上了神秘色彩。用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话说,这乃是美洲现实的“第三范畴”。用另一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吉祥马郎埃斯·罗萨的话说,这叫做“第三河岸”。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内心,一旦你信以为真,它就会产生作用,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历史还是现实。中国人对魔幻现实主义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很能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因此,我本人并不觉得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新鲜的。新鲜的是在那个时代会涌现出这么一大批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为此,我阅读过、研究过、写过。说到马尔克斯的作品,我个人最喜欢的当然是《百年孤独》,其次是更加不事雕琢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却不大喜欢《霍乱时期的爱情》和《家长的没落》。因为前两部有一种于无深处响惊雷的力量,而后两部作品则太过匠气。当然,我说的“无”是相对的,用马尔克斯的话说,《百年孤独》的叙述者无非沿用了外祖母的说话方式,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则撷取了典型的新闻报道或录音采访体。

陈众议称除了《百年孤独》之外,还喜爱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却不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匠气
我注意到寻根派之后仍有不少中国作家或评论家称我们的一些作品为魔幻现实主义杰作。我也粗略浏览过其中的某些小说。这里除了有第一个和第二个把美女比喻为鲜花的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价值迷失和自我放逐。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冤家兄弟巴尔加斯·略萨也成了诺贝尔家族的一员。这无疑为一个时代(或可谓西班牙语文学的第二个黄金世纪)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屈为比附,我曾称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文坛梵·高,巴尔加斯·略萨为毕加索。前者是天才,《百年孤独》犹如神来之笔;后者则是个与时俱进且极富创新精神的学者型作家。
文学的“这一个”与染色体功能
因此,孰轻孰重是文学的问题,也不尽然是文学的问题。俗话说得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文学解读和批评可以强调意识形态,也可以淡化意识形态(尽管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是感性的、印象式的,也可以是理性的和高度理论化的。文学不是用单纯的社会学方法便可以一览无余的,就像心灵不能用此时此刻或彼时彼刻的一孔之见来一概而论。譬如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等,一方面虽非亘古不变,另一方面却又不一定因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变迁。血缘对于亲情、互助对于友情、忠贞对于爱情、思念对于乡情几乎千年不变,尽管其形式在游离,一如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也不再像过去那么稳定。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也在不知不觉地向我们逼近。然而,但凡有亲情、友情、爱情,有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水土在,上述情感将依然是人类的美好诉求。而所谓的自然伦理也不外乎天伦之乐的延伸。如此推演,探究经验与超验、已然与或然、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以及生命的意义和无如,情感的诚挚与怪诞,审美的个性与共性,历史的真实与虚妄,以至语言、阅读、写作、想象本身和人性的类似与迥异、简单与复杂,此岸的困顿与留恋、彼岸的玄想与可能,等等,等等,依然并将继续是文学的使命。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它也是心灵的最佳投影,比历史更悠远、更真切,比哲学更丰富、更具体。人心微似纤尘,大于宇宙。鲁迅谓人心很古,但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惟其如此,文学才是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重要介质;惟其如此,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

陈众议著作《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再版)
“后马尔克斯-略萨时代”的风光不再
至于拉丁美洲当代文学,我指后马尔克斯-略萨时代的文学,固然璀璨依旧,但终究已是风光不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学爆炸”多少得益于冷战,而冷战的结束又多少宣告了资本之外一切皆无。也就是说,物是人非,他们和我们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我们的取向变了。现在我们的市场惟利是趋。人们,尤其是一些青少年放逐自我,甘愿充当由资本打造的形形色色“巨星”的粉丝。当然,拉美文坛也早已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文坛。我说它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率先进入了由美欧所主导的“全球化”的狂欢。如此,不少拉美作家如巴尔加斯·略萨、布里斯·埃切尼克、阿连德等选择了侨居美欧和“国际化”写作路径。这种所谓的“国际化”既有立场和价值观指向,也有题材方面的变数。然而,也有不少拉美作家孜孜于超越马尔克斯等老一辈的光辉。这有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手打造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以及译林出版社和九久公司等引进的不少作品可以为证。
回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缘何有人在这样一个图书市场低靡的时候高价购买《百年孤独》?我想大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每一代读者总会有一些相对钟情于名著的人,这也是各种名著长销(而非畅销)的原因。
是为再版序。
(以上均选自陈众议著《加西亚·马尔克斯传》,2011年再版,中国长安出版社,李念编选并标题,略有删节)
【相关链接】
讲堂报名 | 第125期《让世界认识贾平凹》,顾彬、陈众议、郜元宝、彭青龙、贾平凹畅谈中国现代文学
了解125期嘉宾①|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诗五首:答李白等
编辑:袁琭璐、实习生翁彬婷
责任编辑:李念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